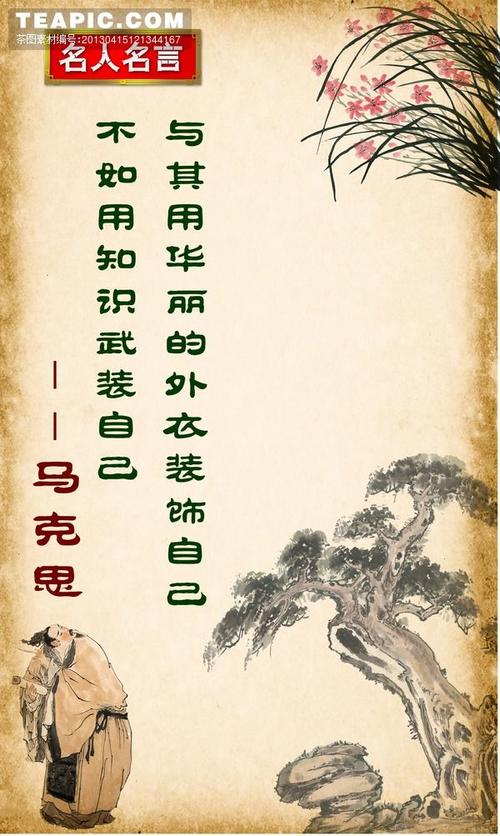
林晓光读《魏晋南北朝》︱“⽂明史”与“政治史”的⼆重奏
⽇本六朝史家、已故京都⼤学教授川胜义雄的名著《魏晋南北朝》(讲谈社《中国の歴史3》,初版于1974年,2003
年出版⽂库本)已由笔者译毕,将与中⽂世界的读者见⾯。在埋⾸于译事之际,作者对历史的宏⼤思考仿佛时时在⽃室
中激起回荡之声,也引发了译者对六朝⽂明的更深体会,以及作者所持“豪族共同体”学说的⼀些思索。
“政治史”与“⽂明史”的⼆重奏构想
不⾔⽽喻,⼈类历史,尤其那些“重⼤事件”的历史总是由权⼒和利益为主导,表现为政治军事上的博弈甚⾄搏⽃(在这
个意义上,政治史,包括军事史,本质上是⼀种权⼒史)。本书作为⼀部断代史,对六朝的叙述也毕竟⽆法不以天下⼤
事为基本的叙述框架。但是,正如作者开门见⼭指出的,魏晋南北朝,是⼀个“华丽的⿊暗时代”。说⿊暗,是因为其在
政治上动荡分裂、战乱频仍,各族之间纷争不已。说华丽,则是因为中国的这⼀“中世”和欧洲的中世纪类似,甚⾄更为
强烈地,在⿊暗时代中开出了华丽的⽂明之花,举凡诗⽂书画、宗教⽂化等等领域,都在这⼀时代发展到了卓越的⾼
峰。“华丽”与“⿊暗”的对举,鲜明地呈现出“政治”与“⽂明”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张⼒互动。这⼀点,从章节的构思上也鲜明
地呈现得出来。在纲领性的《绪⾔》中,作者设置的两个⼩节正是:⼀、“中国史上的乱世”;⼆、“华丽的⿊暗时代”。⽽
全书的头两章则分别题为:第⼀章、“宏⼤的政治分裂时代”;第⼆章、“中国⽂明圈的扩⼤”。像本书这样,开头整整两章
从北⽅的胡族讲到南⽅的蛮族,从东⽅的岛国讲到西域的商⼈,却迟迟不肯开始按部就班叙述史事的断代史著作,恐怕
说得上是凤⽑麟⾓。⽽那正是作者必须要以千钧笔⼒,劈头展现给读者的宏⼤构想所在。在纲领性的这两章中,政治与
⽂明的双轨对峙⼀⽬了然。政治上的⿊暗分裂,与⽂明上的扩散开花,这种“悖论式的现象”,正是全书展开论述的基
点。何以在政治上分裂争乱的“⿊暗时代”,却绽放了如此华丽的⽂明之花?贯穿全书的这⼀核⼼追问,说得更彻底⼀点
的话,其实质就是政治史与⽂明史的交织⽣克,是权⼒史观与⽂化史观的⾓⼒共存。
在我们熟悉的断代史书写模式中,要么就是以经济政治上的⼤事为中⼼组织框架,不遑论及⽂艺余事;要么就是分章罗
列,给⽂学艺术⼀两章的地位,与经济政治等⽅⾯的内容互不⼲涉。像作者gpu超频 这样,在综合性地观照魏晋南北朝这⼀时代
时,同时奏响“政治史”和“⽂明史”⼆重奏的构思,不能不说⾮常罕有。考虑到作者⾝为京都学派东洋史学的第三代中坚⼈
物,不难想到,这当中有着京都学派开⼭内藤湖南独特的“⽂化史观”的深刻浸染。在⽇本战前、战后学界,京都学派这
种以“⽂化”为核⼼理解⼈类历史的⽴场,就曾与重视社会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发⽣过多次论战。不过在此之外,
恐怕还有着作者本⼈更独特的理由所在。川胜义雄作为⼀位⽇本学者,其对本国历史的熟谙⾃不待⾔。⽽他本⼈⼜与欧
洲汉学界交往密切,曾两度前往法国访学;其所供职的京都⼤学⼈⽂科学研究所也汇聚了西洋⽂史哲学的各界名家,故
其对欧洲古典历史⽂化也造诣颇深。故⽽本书虽以“魏晋南北朝”为题,但作者笔触所⾄,却时时超越六朝的时空所限,
⽽是旁及西域,远航欧洲;上溯秦汉,援证东瀛。举凡⽇本平安时代的公卿形态、美国西部⽜仔⽚中的殖民开拓、希腊
罗马时代的地中海⽂化等等,形形⾊⾊可供⽐较视野,帮助理解六朝事象的知识,均被纳⼊作者编织的斑斓图景当中。
不难想见,在这种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巨⼤视野下,作者的思考已不可能仅仅局限在王朝更替、权⼒⽃争等短时段的
纷纭⼈事层⾯。然则在权⼒博弈的事件链条之下,如何勾连融贯⽂明性的思考,让深处潜流的⽂明之⼒穿透表层⽽清晰
呈现?不⾔⽽喻会成为作者解释历史时的重要着⼒点。⽽正是这⼀“政治史”与“⽂明史”的⼆重奏,成就了本书最意味深长
的基调。
“⽂明史”与“政治史”之间相互联结影响,⽽⼜往往并不同步,反倒是此消彼伏,交错搏击,甚⾄成为“祸兮福所倚”式的历
史发展模式。这可以说就作者在本书中给予了最多笔墨,也最有感染⼒的灵魂所在。众所周知,在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之
际,晋琅邪王司马睿⼏乎是⾚⼿空拳渡江南下,在江南延续了晋朝命脉。⽽在当时的江南,豪强林⽴,豪族拥有强⼤的
军事⼒量,⾜可以⾃发组织联军保⼟御敌。然⽽在如此强弱对⽐悬殊的情形下,江南豪族却仍然选择了向司马睿俯⾸跪
拜,⽀持其在江南建⽴起新的流亡政府,并将江南社会改造为西晋式的贵族制体制。在作者看来,其关键正在于北⽅贵
族利⽤晋朝正统权威和先进的乡论主义意识形态压制了军事⼒量占优的南⽅豪族。这可以说是⽂化优势压制了武⼒强权
的⼀个经典案例。
⽽另外的⼀些时候,⽂明则不得不屈服于军政独裁之下。典型的表现,就见于这段壮丽历史的落幕时刻。在南朝陈、北
齐、北周三国衔尾互⽃的过程中,最终由北周撷取了胜利的果实,开创出新的⼤统⼀时代。作者反复强调,在当时的南
朝,已经过梁代⽂化的⾼度成熟,货币经济也发展到异常的⾼度;⽽北齐同时受惠于南朝⽂化和经由突厥⽽来的胡商经
济,也有类似的发展。⽽恰恰是这种经济⽂化⽣活上的发达,使得陈和北齐⽆法消弭各势⼒间的争⽃,只能在沉溺在享
受与内耗中衰弱下去;⽽⼈⼝、经济、⽂化都最为贫弱的北周,却得以平衡、统合胡汉势⼒,打造出军政合⼀的军国主
义体制,击败对⼿。这样勾勒出来的的历史图景,⽆疑会让我们⽴刻想起七百年前上演过的相似⼀幕:正是⽂化落后被
视同野兽的秦国,最终席卷东⽅六国⽽⼀统天下。作者并不回避⼀个基本事实:这种“野蛮”“贫乏”往往会提供缔造⼀个武
⼒强国的原动⼒,使落后国家反⽽可能在政治上军事上战胜发达国家。但同时,他也没有采取在许多学者⾝上习见的那
种⾮此即彼的单线思维⽅式,因为某国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便对其屈膝跪拜,讴歌赞扬其进步性,甚⾄努⼒从中
寻求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这⼀点上,“⼆重奏”式的史观可以说为作者提供了⼀个绝好的平衡点。
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室壁画
当这种“⽂明”vs.“政治”双轨史观被置于更为⼴阔的跨越性视野中时,便唤起了更为深沉微妙的意味。⽂明价值的携带与
重⽣,与政治上的⼀时成败之间,并⾮只在双⽅直接对冲的场合才表现出来。如上所述,作者的思维⽅式有着明显的内
藤式痕迹,但他并未株守前辈的成说,⽽是使这⼀学说延伸到了新的⽅向。如学界已经熟知的,在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
期学说中,东汉⾄中唐被定义为中国的中世时代。从中国内部的社会构造⽽⾔,这⼀时期被认为是贵族⽂化的时代;⽽
从外部同时也是与上古时代相对应的因素来说,则是上古期受到华夏⽂化扩张的刺激⽽成长的异族,反过来压缩华夏,
使之收缩的时代。内藤湖南所观察的版图,在于汉⼈政权与五胡⼗六国。这当然是作者史观的重⼼之⼀,也是他花费了
许多篇幅来着墨的部分。但当眼光越过中国国境内的汉胡之争,进⼀步越过⼤陆边境接邻的塞外异族时,时代性质的判
断却奇异地发⽣了逆转。在第⼆章叙述三韩、⽇本等更外围的“东⽅异族”受中国⽂明刺激⽽成长为国家的视野下,魏晋
南北朝不复是“华夏⽂明内缩”的时代,⽽恰恰相反,变成了扩散和膨胀——
各民族所汲取的华夏⽂明成为了促使这⼀东亚世界成⽴的共通要素;在形成适合各⾃⼟壤的胡族、汉族混合⽂化的过程
中,他们是将汉族⽂明的⼀⽅当作共通媒介来相互联系的。在这⼀点上,不妨说六朝时代是华夏⽂明的巨⼤扩散期;⽽
站在华夏⽂明的⽴场上来看的话,则是其巨⼤的膨胀期。……汉族的政治⼒量衰退期,反⽽成为了汉族的⽂明膨胀期。
(⽂库本页65-66)
在直接与中国接壤,可以武⼒直接取⽽代之的条件下,异族⼊侵造成了政治分裂;⽽在军事⼒量⽆法、或不⾜以直接⼊
侵中国的条件下,异族接受到的便主要是意识形态上更⾼级的⽂明之⼒,这种⼒量牵引着他们的脚步,追随中国⾛上了
建国之路。换⾔之,内藤湖南所注⽬的上古时代华夏⽂明外扩,尽管在中世已转换成了边缘民族的对内反压迫;但在更
外围的世界中,这⼀外扩趋势却仍如涟漪般逐层传递,持续辐射其能量(这也正是内藤史观的内部逻辑)。这样的观
察,不能不说背后仍潜藏着“⽂化史观”的巨⼤威⼒。从政治史的⾓度理解,魏晋南北朝当然是汉⼈政权摇摇欲坠,⽆复
秦汉威光的时代,称之为“内缩”丝毫不错;然⽽在超越了权⼒之争的⽂明⽣医保卡办理流程 命⼒层⾯,尽管发⽣在朝鲜半岛与遥远海岛
上的事情已和某个实际的“中国⼈”或“中国朝廷”⼏乎毫⽆关连,却不可否认正伤感美女 是中国⽂明的能量,宛如通过站站传递的⽕
炬⼀般,穿越天海⽽在异邦创造了历史。这种看不见的“⽂明扩散”或“⽂明膨胀”,⽏宁说在某种意味上更具有恒久的历史
实体价值。
中世知识⼈:联结政治史与⽂明史的平衡点
如前所⾔,本书中的⼀个核⼼命题是“华丽的⿊暗时代”。⽽在这⼀命题之下,通过对⽐⽇本、西欧的历史,作者川胜义
雄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追寻求解,可以说贯穿全书,串联起作者对这⼀时代所有观察、叙
事的脉络:
⼀、在战乱频仍、武⼒称雄的六朝乱世,为何武⼠最终却⽆法(像⽇本中世以后那样)成为稳定的统治阶级,⽽最终⾮
得依靠⽂化统治,向⽂⼈贵族转化不可?
⼆、何以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古典⽂明,在遭受北⽅“蛮族”⼊侵时崩溃消亡,⽽⾯临着相似状况的中国,虽然上古秦汉帝
国同样因北⽅“蛮族”⼊侵⽽陷⼊政治乱局,但古典⽂明却仍然延续下来,甚⾄发展得更为壮⼤?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作者最终寻求到的解答关键,就是六朝时代的“知识⼈”——这个阶层随不同场合及学说,拥有各种
各样不尽重合的变体:⼀般称为“⼠族”“⼠⼤夫”;着重于其⽂化性时⼜是“⽂⼈”;⽤京都学派的术语来说,叫做“贵族”;
⽽豪族共同体论中则称为“豪族”。正是这⼀阶层及其中⼈物,在汉末⼤乱中坚守儒家共同体信念,作为清流⾝遭党锢;
也是他们在五胡⼗六国蹂躏中原时,携带着先进的⽂化技术流⼊东北,将知识和信仰传递到东⽅。在东晋⾯临北⽅强敌
也是他们在五胡⼗六国蹂躏中原时,携带着先进的⽂化技术流⼊东北,将知识和信仰传递到东⽅。在东离婚说说心情短语 晋⾯临北⽅强敌
时,⼒挽狂澜的,是他们当中的王导和谢安;在宋齐下剋上的浪潮中,致⼒于重建新朝秩序的,也是他们当中的萧衍、
范云和沈约。⽽作者的这⼀⽴场,更直接与其所属京都学派的“中世贵族社会论”⾎脉相连,⽀撑在“知识⼈”的背后的,是
那个时代的基本⾻架,门阀贵族社会:
这样的⽂⼈贵族层,超越了国家兴亡⽽长久延续。他们正是在这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明,并进⽽使其发展壮
⼤的中流砥柱。所谓华夏⽂明的强韧性,⼀⾔以概之,正是源于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的强韧性,源于⽀撑着这些知识
⼈的汉族社会的存在⽅式,⽽这与所谓“贵族制社会”是深深地联系在⼀起的。(页9)
然⽽,像这样的⾔论,对⼆⼗世纪以后的中国⼈⽽⾔恐怕是相当陌⽣的,甚⾄多少不免有些“外国友⼈过奖了”的受宠若
惊。试观⼀百年来的史学著作,不管是新⽂化运动催⽣的现代史学,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哪有
⼀种是把这些腐朽没落、百⽆⼀⽤的⽂⼈⼠族当正⾯形象的?不打倒在地再踏上⼀千只脚就已经很幸运了。“创造历史
的是⼈民群众”“东晋南朝的腐朽⽂化需要北⽅游牧民族的新鲜⾎液来拯救”,这些才是我们熟悉的话语。我⽆意于⼀⾯倒
地赞扬作者的这种⽴场,甚⾄对⼀字⼀句地推敲过全书的译者⽽⾔,这种观点都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但这种通过异⽂
明⽐较⽽呈现的声⾳,⾄少可能让我们开始思索⼀些东西:为什么本来应该是救世主的北朝⽂化,却迅速地被南朝毒药
腐蚀同化了?腐朽没落的⽂化形态,为什么会对那个时代的⼈具有如此巨⼤的吸引⼒?这样的东西,真的是那么⼀⽆是
处的吗?如果我们未必还要像五四前辈那样把中国传统⽂化看作⼀⽆是处,那么六朝贵族除了腐朽惰性的剥削⽣活,除
了对家族门阀的顽固维护之外,他们的⾝上是否也有着值得肯定的⽂明价值?
当然,作者尽管如此“反弹琵琶”式地论说了贵族及贵族⽂化的正⾯价值,却也并未就此拜倒在他们裙下,⼀味讴歌不
已;⽽是清晰地体认到他们在精神⽂明层⾯的坚韧厚重,与政治层⾯上的软弱失败,是⼆者并存的。正如第⼋章叙述侯
景之乱后贵族阶层的没落,作者深有感触地渲染了贵族们因失去实际政治经济能⼒⽽⽆⼒应对残酷现实的惨象。陈朝虽
然还有若⼲王谢⼦弟担任⾼官,但却已不复能对实际政事发挥作⽤——
这⼀班乡野武⼠之所以要待残存的若⼲贵族以⾼位,不过是想替他们的政府添上些壁花龛炉般的⽂化装饰罢了。因为在
荒凉的战乱之后,还能传留昔⽇黄⾦时代所凝练的⽂化⽓息的⼈物,毕竟还是有他们的稀缺价值。对距离⽂化遥远的乡
野武⼠来说,这种东西令⼈轻蔑,有其弊端,然⽽另⼀⽅⾯,这毕竟⼜象着征令⼈⼼折的美的价值。(页287-288)
这种评论既正视了贵族已堕落成历史刍狗的现实,⼜对其曾经作为历史主体的辉煌绚烂深怀惋惜,不因此⼀笔抹杀其所
代表的⽂化价值。政治史视⾓与⽂化史视⾓在相互碰撞的同时⼜相互融合,照亮了复杂纵深的历史地层。对六朝⼠族这
种深沉⽭盾的喟叹,在中国史家笔下同样不容易见到;然⽽在⽇本史著作中,类似的感触却随处可见——被中世武⼠取
其位⽽代之的天皇与贵族公卿,正是在⾼贵地位的外观装饰下,作为⽂化摆设过着⿊暗贫困、寄⼈篱下的痛苦⽣活。这
与南朝贵族的遭遇可谓异曲同⼯。⽽著名的⽇本⽂化史家家永三郎更在《贵族论》中指出:贵族⽂化⼀⽅⾯逐步被新兴
的武⼠⽂化所取代,然⽽另⼀⽅⾯,由昔⽇光荣结晶成的贵族⽂化,却仍然在多⽅⾯成为武⼠⽂化艳羡取法的典
则,“贵族⽂化即使在离开了贵族阶级这⼀社会性根基之后,仍然渐次为新兴指导阶级的⽂化建设注⼊丰富的营养,以
此对⽇本⽂化的发达做出贡献”。政治史与⽂化史的分别实现与价值错位,在此得到了微妙的呈现。
未完成的学说:“贵族-豪族”还是“知识⼈”?
熟悉京都学派东洋史学的读者应当不难想及,这种以“知识⼈”为历史焦点的思考⽅式,与⾕川道雄、川胜义雄共同提倡
的“豪族共同体论”必定有着深层的联系。这⼀学说认为,六朝时期的地⽅豪族由于受到来⾃乡村共同体的抵抗,⽽⽆法
彻底发展为封建领主,不得不转向与⾃耕农妥协共存之道,负担起⽂化指导的职能,发展为⽂⼈性的贵族。⽽“中世知
识⼈”,不妨说正是这种“豪族—⽂⼈贵族”的另⼀种表述。
当然,这⼀学说是否真的能够普遍成⽴?⽆论⽇本还是中国学界都⼀直没有停⽌过质疑反思之声。包括这种⽥园式
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是否⾜以概括当时豪族与⾃耕农的关系,⾃耕农阶层同样壮⼤的其他时期为何没有催⽣出类似的
贵族阶层等,都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同样容易惹起当今六朝史学者(尤其偏重于北朝研究者)的商榷的,是本书中
作者针对⼗六国⾄北朝⼀脉所采取的理解⽴场。和当代中国史家相⽐,作者在这⽅⾯的⽴场⽏宁说更接近于中国的传统
史家——汉⼈⼠⼤夫代表着更先进更⾼等级的⽂明,⽽胡族国家则有其体质上难以回避的先天性缺陷:所谓“宗室性军
事封建制”,使得五胡各国始终⽆法摆脱部族强⼈内部⾃相残杀,政权堕落为各谋私利⼯具的命运。这⼀命运,每当胡
族统治者接受汉⽂明程度较深时,例如苻坚和魏孝⽂帝的情形,便较可避免(但相应地则会产⽣过度理想化⽽⽆视现实
的弊病)。这⽆疑是把汉⽂明当成了那个时代的最⾼标准,⽽将其他种族社会置于学习者的⽴场。不论学习了汉⽂明后
会成功还是会失败,在作者的历史想象中,时代的⽬光总是汇聚流向汉⽂明这⼀辉煌中⼼的。这样⼀种具备鲜明的⽂明
价值评判的视⾓,恐怕不免于为今⽇的相对论者所讥。
不过,如果像作者⼀样,将中国-边缘异族-周边异国结合成⼀个⼤型的⽂明涟漪来看待的话,他的这种想法也就未必那
么难以理解了。⽆论我们今天如何痛烈地⾃省也好,信奉⽂化相对主义也罢,在⼀千多年以前的东亚世界,中国相对于
周边各国,作为⽂明中⼼⽽被仰视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是不以后世⼈的价值审判为转移的。⽽相对于五胡⾊彩浓烈
的北朝,南朝当然是较多地保存了所谓“华夏正统”因素的⼀⽅。换⾔之,如果选择“政权”“⼈民”等⾓度切⼊,我们对南北
朝史的诠释可以完全不同甚⾄对⽴于作者;但只要和作者⼀样以“知识⼈”所肩负的⽂明为核⼼去理解历史,恐怕很难不
朝史的诠释可以完全不同甚⾄对⽴于作者;但只要和作者⼀样以“知识⼈”所肩负的⽂明为核⼼去理解历史,恐怕很难不
得出和他相似的结论。关于爷爷的作文 ⽴场的分歧,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视域的差异,是将什么和什么放在⼀起来衡量⽐对的问题。东
晋南朝的孱弱,在与⼗六国北朝的战争胜负中会⽆可辩驳地呈现出来;⽽东晋南朝的强⼤,却要放在与东亚各国的⽂明
影响关系中才能看得透彻。
和这种可以基于⽴场转换⽽消解的观点差异相⽐,本书⽏宁说透露出了川胜史学与“豪族共同体论”之间更深层次、更具
必然性的理论架构内部⽭盾。那就是,六朝时期的⼠族,到底是应当从豪族-贵族,亦即掌握地⽅-中央权⼒(包括政治
经济乃⾄⽂化的权⼒)的特权阶层⾓度去理解;还是更应当从教养⼈-知识⼈,亦即作为⼀种⽂明中⾝负⽂化价值的特
定阶层去把握?
在本书中着⼒抒写的,正是后⼀种以⽂化辐射⼒为准则的探索⽴场。这种⽂明之⼒的坚韧担当,让秦汉古典⽂明历经战
⽕⽽在江南延续重⽣;这种⽂明之⼒的崩溃流散,则将⽕炬传递到了中国周边的后发⽂明⼿中。在这种论述思路
中,“知识⼈”其实已经超越了社会科学中所界定的特定社会阶层,⽽成为了⼀种符号性的“⽂明”表现者和担当者。这⼀阐
发实际上和⼀般所理解的“豪族共同体论”已经有了相当重要的分歧——尽管这种分歧已经通过作者尽可能巧妙精致的论
述,被⼩⼼翼翼地弥合起来了。“豪族共同体论”强调的是乡⾥社会中的豪族与⼩农之间的共同体关系,这种关系中的⼀
个重要侧⾯固然是豪族作为“⽂化指导者”居于⼩农之上,得到⼩农的信服追随,但这种⽂化形象是被置于“豪族—⼩农”的
相互关系中展开的。所谓“豪”本⾝并不必然包含着“⽂”这⼀素质,⽏宁说在汉语语感中,这两者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所
谓豪族和⼩农之间是否真是如此普遍地存在这种⽥园式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也正是过去中⽇学界对这⼀理论抱有疑
虑的原因所在。诚如作者⾃⼰在第三章中所着重论述的,“豪族”并不都是维护乡⾥共同体,坚守儒家伦理的⽂化型⼠⼤
夫;⽽反过来,有⽂化的⼠⼈反⽽往往是清贫隐居的“逸民”,甚⾄像郑⽞那样起⾃傭⼯的⼤学者。因此“豪”与“⽂”之间其
实是⽆法等同视之的,只是在⼀定范围内重合在相同⼈群⾝上⽽已。当这⼀关系被限制在共同体论内部关系的⼀个侧⾯
看待时,并不会发⽣严重的问题(不⽂的豪族会被视为共同体的破坏因素⽽被排除出这⼀关系),但如果将“⽂化⼈”“⼠
⼤夫”从中抽取出来,独⽴作为时代的中⼼要素予以观察时,事情就变化了。因为此时“⽂明”及⽂明的守护者“⼠族”⾯临
的就不仅仅是“豪族—⼩农”关系,⽽是来⾃四⾯⼋⽅的各种关系——⽂化统⼀与政治分裂、⽂明捍卫者与破坏固有⽂化
秩序的“蛮族”、先进⽂明与后进⽂明的提携与摩擦、⼈⽂中⼼与边缘流散、国境焦虑症的特征 之内与四邻周边……其所涉及的关系远
远超出了豪族共同体论固有的论域,⽽演进为⼀种新的⽂化史观。⽽这才真正是本书所着⼒书写的⽅向。
就这⼀意义来说,我们实在不免要为川胜义雄感到惋惜,因为他原本⼤可以发展出⼀套超越共同体论的学说,旗帜鲜明
地为六朝史提出⼀个更富有延展性开放性,同时也更符合六朝⽂献特性的观察焦点——毕竟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材料,正
都是由这⼀阶层⾃⼰来书写的。但他却最终未能摆脱这⼀框架,⽽使得⾃⼰的学说停滞在了⼀种蜕变不完全的中间形
态,也使相关论说出现了摇摆游移的缝隙。
那么,作者为何没能直率地以“知识⼈”的⽂明史来搭建⾃⼰史观的基本框架呢?可以考虑到的理由包括两描写秋的作文 点。其⼀,当
然是他和⾕川的深挚友情。两位战友⼀同探索出来的豪族共同体论框架弥⾜珍贵,假令——只能是假令——作者真的已
经意识到⾃⼰思想的展开⽅向未必与豪族共同体论完全⼀致,恐怕他也狠不下⼼来出⼿挑战这⼀理论,⽽会宁可选择在
既有学说框架下微调。这⾃是⼈之常情,不难理解。其⼆,也许更严重的制约来⾃那个时代的⼤环境。那是⼀个马克思
主义史学占据绝对主流的时代,“⼈民群众”才是⽆可置疑的历史主体、历史推动⼒。“知识分⼦”怎么能被当成历史主⾓
呢?在《结语》中,作者其实已经委婉地表达了这种⽆奈:
“推动历史的是⼈民群众”,这是⼈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号。⽽在本书中,我⽏宁说却是将重点置于⽂明的中坚承担者,
⽂⼈贵族/知识⼈的⾝上戴望舒代表作 ,去追踪历史的展开。这⼀⽴场或许会招来⾮议,以为是在与上⾯的⼝号反其道⽽⾏之。然⽽,
如果只是⼀味地把“民众”“⼈民”之类的词汇抽象出来夸夸其谈,“推动历史的⼈民群众”的具体形象却反⽽会在不知不觉中
消失不见。要真正接近过去时代的“民众”,唯⼀的办法就是时常关注:民众的意志在种种历史现象当中,究竟是以怎样
的具体形态展现的?(页427)
⽆法公然挑战“⼈民史观”的作者,只能采取迂回战术,声称⼈民群众固然才是推动历史的真正⼒量,然⽽六朝史料中却
根本未曾留下多少“⼈民”的痕迹,为了避免抽象空谈,知识⼈正可以视为“民众意志”在历史现象中展现的“具体形态”反映
——归根结底,不就是因为⼈民群众选择了知识⼈来作为他们的指导者,知识⼈才得以维持如此强⼤的⼒量吗?
这种辩论逻辑在今天看来,已经迂阔得有些可笑。然⽽⾝处那个时代的川胜们,却只能采取这样曲折隐晦的苦⽃姿态。
川胜学说体系中的暧昧之处,⾄少相当程度地应该在这⼀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予以把握。时⾄今⽇,我们也许已经⾜够
幸运,⽆需像作者⼀样为了说服⾃⼰配合“⼈民史观”⽽烦恼;因⽽也就应该更能够剥去具有时代性的修辞外⾐,直接前
往作者真正希望抵达的新起点。在这种新的学说中,阶层、集团、⽣产关系实际上都已经让出了核⼼⽀点的位置,“⽂
化”的⼒量、“⽂明”的延续,成为了各种⼒量缠绕作⽤的中⼼光点。这显然不是六朝史研究的唯⼀可能出发点;但是,只
要采取和作者同样的⽐较⽂明、⽐较历史视野,这⼀命题就会顿时光芒四射地凸显出来,成为我们⽆法回避的根本性追
问焦点所在。这或许就是本书留给我们的,最为余味深长的展望课题吧。
(本⽂来⾃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本文发布于:2023-03-19 13:01:12,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67920207337122.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那晓光.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那晓光.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