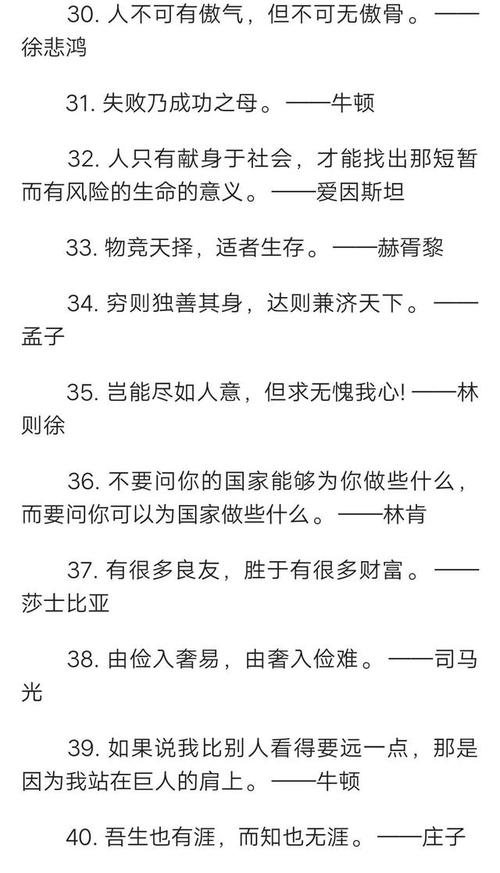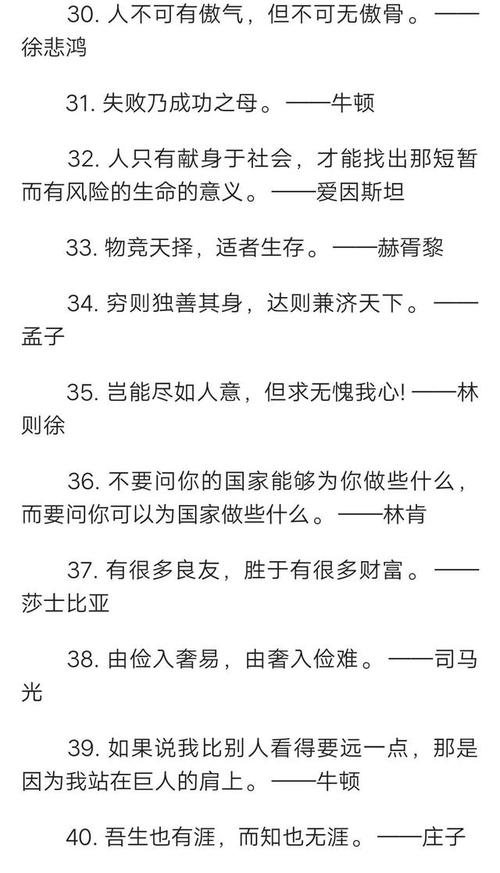
“洞”中青年的“武侠梦”
郭沫若先生说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1]文艺是在无之中创造出有,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
[2]文艺创作从未终止,却少有人批评,使得至少半数的作家偏重“量”,迎合大众,却忽视了“质”的重要性,伴随着社会对文学变革的需要,批评数量增加却多缘于利益目的,出发点并非是使文学本身受益,用王安忆的话来讲——批判人性从故意变成了乐趣。因此,以真正关注文学作品社会意义与召唤赤诚之心为目的出发,创造有利于文艺发展新方向的批评在当今社会势在必行,70后作家群体作为最热门的关注对象理应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然而逐渐成为文坛的“中坚代”力量的70后,却不可避免的在创作中走向趋同。底层叙事、人性剖析、城乡矛盾屡见不鲜,许多作家在获奖的快感中丧失创新性,在自己定好的轨迹上越走越远,以大众的喜闻乐见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尺,文学逐渐失去其独特性和深刻性。
在当代文坛,很难见到五六十年代如莫言、苏童等代表性作家个体,但田耳却在70后作家中表现的特立独行。李敬泽说他是一只文字世界里狡猾的狐狸,几乎所有70后作家都有自己的固定风格,个性鲜明,而田耳却没有,任谁也无法预测他下一次的创作,这也正是他的独特之处。
田耳凭借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同时,由于拥有纯文学中难得的“好看”特点.他的作品逐渐进入大众读者的视野[3]。
相关研究络绎不绝,但具有综述性质的创作论只有三篇,以其中篇、长篇和短篇作为分类,其他学术研究均以期刊形式出现,对于整体探索田耳创作内容和风格仍有研究空间可寻。本文以田耳最新长篇力作《下落不明》为线索,先造一座佴城,了解田耳创作的精神乐园,整体把握其独特的乡土意识;再破一桩案件,理解田耳最擅长的破案写作模式;在江湖中探寻田耳的“道义”概念与“老大”群像;在《下落不明》的作品细读中体会田耳文学创作的归途;全文整体探索田耳创作中独一无二的“无赖”气质,对田耳的创作内容和写作风格有新的把握。